紧抿上唇,隐藏真实情感,就可以拥有世界?
- 股票
- 2025-04-06 10:50:03
- 26
1895年5月26日,奥斯卡·王尔德“严重猥亵罪”罪名成立,被判处两年监禁和苦役。当王尔德离开被告席时,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同年晚些时候,在从伦敦转监雷丁的途中,王尔德穿着囚服、戴着镣铐,在克拉珀姆( Clapham) 枢纽火车站的月台上站了一会儿。人们开始认出这位名誉扫地的作家,纷纷嘲笑他。王尔德在狱中长信里写道:“在11月的阴雨中,我站了半小时,周围是一群嘲笑我的乌合之众。”这封信的一部分后来以“自深深处”为题出版。“在那件事之后的一年里,我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哭泣。”这是王尔德为自己设计的含泪的纪念仪式。19世纪90年代,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研究案例中,一位病人也做了相似的事。“一个人在狱中不哭的一天,”王尔德写道,“是他内心坚硬而非快乐的一天。”身陷囹圄和痛苦的王尔德继续从基督教中汲取有关哭泣的思想。在《雷丁监狱之歌》中,“被处以绞刑的人”(一名因杀害情人而被处以极刑的囚犯)的眼泪具有一种基督救赎的力量:
因为只有血才能将血擦去,
只有眼泪才能治愈:
该隐的深红色印记,
成了基督雪白的封印。
其他狱友用泪水表达自己的怜悯的悲叹:
我们流的泪就像熔化的铅,
为了我们还没流的血。
爱尔兰裔、柔弱、颓废,还有一丝罗马天主教的气质:奥斯卡·王尔德和他的眼泪属于19世纪末男子气概和情感类型的一个极端。他的宗教和文学感伤与新帝国男性的坚忍和尚武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
1895年12月底,苏格兰殖民官员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 Leander Starr Jameson )率军从英国的开普殖民地进入德兰士瓦( Transvaal ),企图煽动英国定居者起事反抗布尔统治者,但以失败告终。詹姆森因领导这次突袭的方式而受到责难并被短暂监禁,但他仍然成了一名帝国英雄和英国人努力、坚忍、勇敢的模范。他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一首诗提供了灵感。这首诗发表于1910年,它仅以《如果——》为题,但比其他任何作品更好地提炼出英国人紧抿上唇的精神。1995年,在詹姆森突袭过去整整一个世纪后,即作为一种民族特征的紧抿上唇消失几十年后,由英国广播公司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吉卜林的《如果——》是最受英国人最喜爱的诗。
吉卜林在他死后出版的自传中写道,这首诗“源自詹姆森的品质,包含了成就卓越所需的最显而易见的建议”。该诗以父亲给儿子提建议的形式写成,包含一长串条件句,诗的开头是:
如果所有人都失去理智,咒骂你,
你仍能保持头脑清醒;
如果所有人都怀疑你,
你仍能自信不改,并宽恕他们的猜忌
父亲给出了进一步考验忍耐力和自控力的方法:
如果你是个追梦人——不要被梦主宰;
如果你是个爱思考的人——不要以思想者自居;
如果你遇到骄傲和挫折,
把两者当作骗子看待
最后的对句在1923年被刻在了温布尔登中心球场运动员入口的上方,至今依然在那里。 在《如果—》中,儿子被要求对外界事物保持超然独立的态度,对他人亦应如此:
如果他人的爱憎左右不了你的正气;
如果你与任何人为伍都能卓然独立
多重条件句将读者的胃口吊到了最后。这个卓越非凡、坚如磐石的人,既然冷若冰霜到如此地步,他又能获得什么回报呢?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能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成为大英帝国的继承者:
你就可以拥有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全都归你,
更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你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吉卜林不仅是詹姆森的好友和崇拜者,还是1899年至1902年布尔战争中其他重要人物的好友和崇拜者,其中包括塞西尔·罗兹( Cecil Rhodes )和阿尔弗雷德·米尔纳( Alfred Milner )爵士。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为1910年大英帝国南非联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如果——》正是在这一年出版。吉卜林的独子约翰那年13岁。四年后,当帝国大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威胁时,约翰·吉卜林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勇气。即将迎来30岁生日的奥斯卡·王尔德之子西里尔是一名军人,他也要走上战场。生于爱尔兰的王尔德和生于印度的吉卜林,以及他们儿子的眼泪、想法和经历,能帮助我们理解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帝国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的时期,“紧抿上唇”的心态是如何被创造、被抵制和被检验的。
“紧抿上唇”这句话起源于美国。1871年,即《一年四季》杂志的创刊编辑查尔斯·狄更斯去世的第二年,该刊发表了一篇介绍“美国流行短语”的文章,如此解释“保持上唇紧抿”:“对目标保持坚定,坚持自己的勇气。”这并非该短语唯一的含义,它还表示拥有高度的自尊心、独立性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即使在19世纪末,英国读者也不确定这句话的内涵。它常常出现在引号中,有时仍被视为美式语言。 但是从布尔战争时期开始,特别是在有关国际关系和战争的讨论中,这句话变得越来越常见,它的内涵逐渐落到一个核心品质上,即在面临考验和困境时表现出勇敢并能隐藏自己真实情感的能力。 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更广的文化范围内,英国经历着从感伤主义向禁欲主义和情感克制的转向,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正在崛起。 “紧抿上唇”的价值理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流行起来的。
甚至在“紧抿上唇”作为一种理念出现以前,英国教育机构就一直在培养男孩和男人自控和克制情感的能力。这种普遍的做法并不局限在公立学校。对有些人而言,训练从出生就开始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的育儿手册警告称,婴儿是哭哭啼啼的暴君。明智的父母不会纵容孩子任性的眼泪,而是以身作则,教他们如何“默默忍受,控制自己,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或女主人”。后来被送到寄宿学校的男孩,必须学会如何处理因分离而产生的情绪。答案通常是不去谈论它们,甚至不去感受它们。英国国教会为来自不算富裕家庭的孩子开办的日校里也盛行类似的风气。19世纪70年代,据英国米德兰兹地区一所日校的学生回忆,孩子们会因各种微小过失而被老师用藤条殴打,然而“饮泣吞声是一种荣誉”,“如果一个男孩忍不住流泪,他可以将脸藏在怀里,从而避免受到嘲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同样的态度——希望用不哭的方式克服情绪和身体上的痛苦——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存在于许多学校中,它的某些方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哈丽雅特·马蒂诺在1840年出版的小说《克罗夫顿男孩》是早期校园题材小说的代表,这类小说后来因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1857年出版的《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和鲁德亚德·吉卜林1899年出版的《斯托基公司》而闻名。 哈丽雅特·马蒂诺笔下年轻的主人公休斯被送到克罗夫顿学校前,有一次他在家艰难地学习功课,哭喊着要睡觉,他希望自己成为克罗夫顿的一员:“他认为克罗夫顿的男孩都能以某种方式完成功课,这是毋庸置疑的;然后他们就可以睡觉了,没有任何不开心的感受,也不会流泪。”初到学校,一个男生给小休斯提了一些建议:“你会发现在英国的每所学校,男孩不应该谈论感受——任何人的感受。这就是他们从不提及自己的姐妹和母亲的原因——除非两个亲密的好友在一起时,要么在树上,要么在草地上。” 如果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克罗夫顿男孩,男孩建议休斯谨言慎行,“充满行动力”,表现出“男子汉气概”但不为此骄傲。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儿童文学为哭泣引入了一个新词语——blubbing( 哭鼻子 )。该词在19世纪60年代被首次使用,它是紧抿上唇兴起的另一个标志。使用该词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来自1868年《比顿男孩年刊:事实、小说、历史和冒险卷》刊登的一则故事。故事中的男孩为另一个男孩的眼泪感到尴尬,他试图让后者振作起来:“好啦,不要哭鼻子了,你有一个好伙伴。”当对方继续哭泣时,他几乎无法忍受,于是“哽咽地”安慰对方,虽然“离开家人第一个夜晚的感受非常奇怪”,但假期不远了,而且他们俩可以成为朋友。 随着公立学校教育日益普及和严格,在这一时期的现实和虚构故事中,“不要哭鼻子”无疑是许许多多男孩给出的劝告。 1915年5月,萨里郡查特豪斯寄宿学校的一名10岁学生杰弗里·戈尔的朋友和老师可能就说过这番话:戈尔在早餐时得知,他的父亲因乘坐的“卢西塔尼亚号”被一艘德国潜艇击沉而命丧大海。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头的老师宣读了晨报上的战争新闻,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则新闻与小戈尔的关系。戈尔回忆道,当他听到这则消息时,“身体几乎颤抖”,然后突然“情不自已地抽泣”。他记得自己获得了安慰,但如同病人一般。人们在他面前停止了交谈,此后再无人直接提及死亡。

《银翼杀手》剧照
英国的精英教育机构旨在通过将古典教育和团队体育运动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克己能力、良好的举止和爱国主义精神。一份报纸在对1925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年度橄榄球赛的报道中赞美了观众良好的举止:“在任何地方,比赛双方制造的激情都受到了压制。”报道总结道,这是一场盛大的“紧抿上唇的游行”。 1936年,《泰晤士报》一篇关于中国“流泪党”的文章将东方人的情感与抑制泪水这一“英国传统”进行了比较:“当小孩哭泣时,他们被要求停下来。在公立学校,甚至更早的时候,哭鼻子是自取其辱。”文章写道,一个年轻人在大学结束时可能会在公告栏上看到自己糟糕的考试成绩,他等待泪水盈满眼眶,却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流泪的能力。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完成了英国绅士的教育。《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一点遗憾。E. M. 福斯特曾哀叹英国公立学校培养的年轻人“有强健的身体、聪慧的头脑、不成熟的心智”。 然而直到“二战”结束以后,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开始呼吁男孩少受压抑情感的教育。我们看到,其中一人正是杰弗里·戈尔。他长大后成了一名人类学家,对英国民族性格和情感压抑尤其感兴趣。
“二战”期间和结束之后,英国人因“紧抿上唇”而闻名于世。但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英格兰人—通常是参加过战争的男性—尤其被认为是冷酷无情的紧抿上唇者。1937年,这一观念得到了强化。由弗雷德·阿斯泰尔、琼·方丹、乔治·伯恩斯和格雷西·艾伦主演的好莱坞音乐喜剧《困境中的少女》中,有一首由乔治·格什温和艾拉·格什温创作的歌曲《紧抿上唇》,这首歌用饱满的热情嘲讽了英国人的精神。格雷西·艾伦唱道:
是什么让伊丽莎白女王
成就如此伟业?
是什么让威灵顿
在滑铁卢建立功勋?
是什么让每个英国人
成为彻头彻尾的斗士?
不是烤牛肉、不是麦芽酒、不是家,也不是母亲,
而是他们传唱的一件小事:
紧抿上唇,勇敢的小伙子,
坚持不懈,老豆子。
振作起来,继续蒙混过关!
毫无疑问,这不是严肃的文化分析,但这支口水歌配上精心编排的奥斯卡获奖舞蹈,浓缩成了一种令人难忘的形式。对广大国际观众而言,这是一种以各种形式流传了数十年的印象。 一句令英国观众陌生的美式短语,变成了向美国观众解释英国人的习语,紧抿上唇完成了一次循环。
对不列颠群岛上的居民来说,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地区之间情感风格存在差异。18世纪的复兴派教会及其信徒精神觉醒时的身体表现,在工业与农村地区都引人注目,这些地区包括英格兰西南部和东北部以及威尔士的工人社区。在那里,包括乔治·怀特腓德和丹尼尔·罗兰在内的循道宗牧师“用热情点燃了狂热的威尔士人”。 20世纪初,威尔士人依然以易激动而闻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自由党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1909年,劳合·乔治担任财政大臣。为了实现他的“人民预算”、提高税收、新增社会福利等主张,他在议会两院与反对党进行斗争。1909年12月,劳合·乔治在自己所在的卡纳文自治市选区的一间教室里举行集会,正式宣布自己愿再次代表选区参加次年大选。劳合·乔治获得了人们的满堂喝彩。他饱含深情地讲述了自己在上议院与反对者的斗争、将更多“克伦威尔精神”灌输给英国民众的愿望,以及他作为威尔士人和“大山之子”的身份。当观众起立欢呼时,劳合·乔治泪流满面,几乎无法完成演讲。当他向会众致谢时,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不论劳合·乔治意识到与否,他在公共场合流泪的行为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某种政治风格的延续。
这件事被广泛报道,不同地区的报纸,侧重各不相同。苏格兰的《邓迪晚间电讯》相对克制,但确信此事反映了财政大臣的民族特征:“集会一开始就爆发出威尔士人的热情。集会结束时,观众被威尔士人炽热的情感所征服。”《赫尔每日邮报》公开反对在一群“疯狂的威尔士人”面前“展示过度的情感”。它指出,“在民众头脑清醒、沉着冷静的约克郡,这种展示足以让大厅里的人走空!”该报社论强烈抨击劳合·乔治的预算方案,并将人们对他威尔士式的眼泪及其“信仰复兴主义”和“浮夸和狂热的民族性格”的厌恶作为反对他的另一个理由。 五年后,基齐纳( Kitchener )勋爵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对劳合·乔治提出在战争爆发后招募一支威尔士军团与其他地方部队并肩战斗的设想持保留意见。他对自由党首相阿斯奎思( H. H. Asquith )说,威尔士人“粗野放荡、不服管教,需要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严厉对待之”。基齐纳的质疑并未奏效,一个威尔士团真的组建了起来。但有趣的是,这个上唇蓄满胡须的男人,正是那幅以“你的国家需要你”为口号的著名征兵海报的主角,他认为本国某些地区男性的坚忍品质,使他们比其他地区的男性更加不可或缺。
随着冲突的持续,国内外的作家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英国士兵(或称“汤米”)具有一种特殊的坚忍冷漠的品质。玛丽·范·登·斯蒂恩( Marie van den Steen )伯爵夫人是一位贵族、护士和教育家,她是1907年在布鲁塞尔开办的一所天主教护理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同年在布鲁塞尔开办的另一所与之竞争的自由主义护理学校的校长是坚忍不屈的英国女性伊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战争爆发后,比利时的范·登·斯蒂恩伯爵夫人在法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了英国士兵的性格特征。《利物浦回声报》刊登了译文,并起了一个引以为傲的标题:《 不动感情:我们汤米的性格素描》。该文的中心思想是英国人“冷漠无情”,范·登·斯蒂恩用传统和相对缺乏想象力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解释。她认为英国人“对情感只有最细微的反应”,但这种细微的情感是真诚的。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沉默矜持的品质,连同自我牺牲和体育竞技精神,在英国士兵身上结合在了一起,最好的象征是当炸弹落在他周围时,他依然漫不经心地抽着烟斗:“烟斗是自我控制的象征!他烟斗里冒出的白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徽章。它表明脉搏稳定,呼吸正常,头脑清醒。”
当然,这些都是宣传,目的是在战争时期提振士气和促进国家恢复;正是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复不断的宣传,人们开始相信英国人紧抿上唇的特性。但是,现役军人真实的情感生活,相比处变不惊、乏味无趣、漫不经心地抽着烟的汤米们更加动荡不安。诗人兼小说家弗雷德里克·曼宁参加了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战争的自传小说《命运的中间部分》。在书中,当目睹自己战友的残肢断臂和尸骸时,男人们流下了眼泪,他们震惊、难以置信、痛苦不堪。一位名叫普理查德的士兵向他人讲述了身负重伤的战友的生命最后时刻,这段描述捕捉到了一种同时表达、抑制真实和痛苦的感受的尝试:“泪水从普理查德僵硬的脸上流下来,就像雨滴从窗玻璃上滑落一样;但他的声音没有颤抖,只有玻璃破碎时男孩发出的那种不自然的高音。”士兵的眼泪有时甚至会出现在报纸新闻中,尽管它们更像是宽慰而非痛苦的眼泪。《每日镜报》1916年6月报道,一列满载英国受伤战俘的火车在伯尔尼移交时,受到了成千上万的瑞士祝福者的欢迎,他们向士兵报以欢呼和鲜花,当地乐队演奏了《天佑国王》。报道这一幕的英国外交官在谈到受伤士兵时说“:他们中有许多人哭得像孩子一样;一些人激动得晕了过去。一位士兵告诉我‘:先生,上帝保佑你!这仿佛是从地狱掉进天堂。’”
帝国军人并不总是克制情感。 事实上,履行职责时所需的夸张的坚忍精神,以及通过沙文主义神话和宣传所强化的坚忍品质,为宣泄情感制造了更大的需求,但这不得不在私下进行。在剧院昏暗的半私密空间里,或者在秘密的私人会面中,军人可能会流泪。剧作家沃尔福德·格雷厄姆·罗伯逊( Walford Graham Robertson )的圣诞剧《萍琪和仙女》( Pinkie and the Fairies )1908年在伦敦国王陛下剧院首演,该剧由明星艾伦·特里( Ellen Terry )领衔主演,大获成功。罗伯逊想要抓住孩子们的心,毫无疑问他做到了,但他不经意间也赢得了军人的追捧—“夜复一夜,国王陛下剧院的售票台前看起来就像奥尔德肖特( Aldershot )的游行队伍”。他询问一位士兵朋友,这部剧对军人是否有吸引力。士兵告诉他,他们来此就是为了流泪,而且给他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孩子对仙境的幻象逐渐消失的那一幕。夜复一夜,在昏暗的国王陛下剧院,士兵们为萍琪、仙女和她们消失的仙境而哭泣,“灯光照在一排排被泪水沾湿的衣襟上”。 这部戏不仅令士兵着迷,可能还吸引了水手:它后来在朴次茅斯和伍尔维奇上演( 见图17 )。
这种动情行为也发生在英国最有权有势的阶层。埃莉诺·格林( Elinor Glyn )夫人是一位文笔生动的浪漫小说家。她的男性崇拜者包括布尔战争期间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1903年,他们在波西米亚的温泉小镇卡尔斯巴德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米尔纳在晚上的一大乐趣——尽管格林夫人未必感兴趣——是大声朗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尤其是《斐多篇》,“这本书的最后几页总能让他感动落泪”。这几页记录了苏格拉底之死,他告别朋友和家人,平静地喝下狱卒为他准备的毒药。就像士兵们为萍琪和仙女哭泣一样,这幅生动的场景有力地提醒我们,我们对这一时期英国男性受压抑的认识是不完整的。这是英国男性为他人的饮泣吞声而潸然泪下的绝佳案例,亦是紧抿上唇时代的典型产物,它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绎,时至今日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在《斐多篇》末页,苏格拉底斥责他的好友像妇人一样恸哭,自己坚持从容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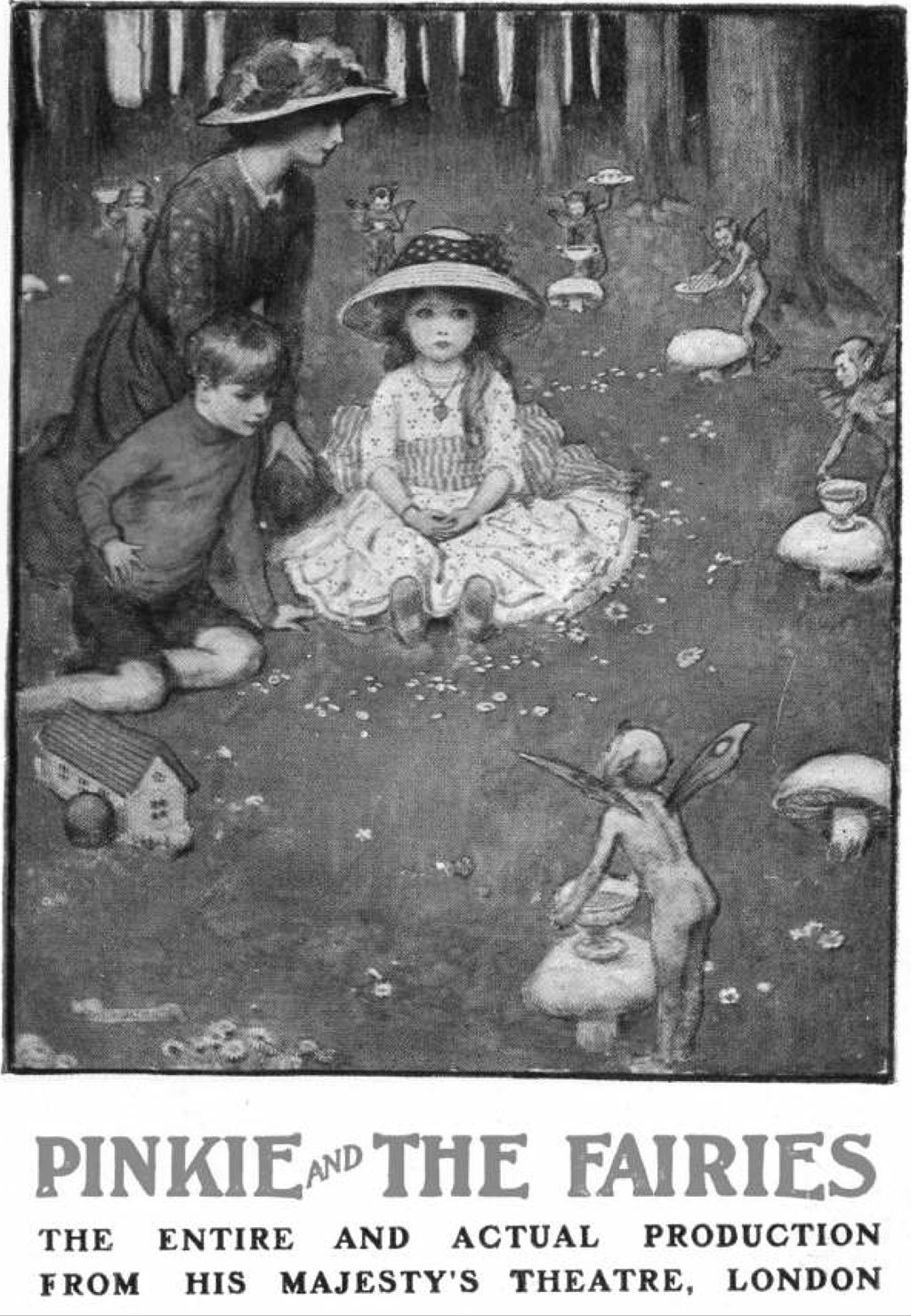
1910年,沃尔福德·格雷厄姆·罗伯逊创作的圣诞剧《萍琪和仙女》将在伍尔维奇皇家炮兵剧院上演的海报。
在本章开头,我将奥斯卡·王尔德和吉卜林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不同类型的男子气概的代表进行了对比——王尔德是感性的唯美主义者,吉卜林则是坚忍的帝国主义者。但事实常比这种对比复杂。王尔德和吉卜林生活并活跃在同一个文化世界中。奥斯卡·王尔德是吉卜林小说的崇拜者;他送给儿子的最后一件礼物——1895年的刑事审判使王尔德和他的小儿子从此永别——是一本吉卜林的《奇幻森林》。 吉卜林的文学作品和思想态度并非总是不带感情的。他的早期小说《抛弃》成书于1888年并在印度出版,它讲述了一位娇生惯养的年轻英国男子,在印度面对军营生活的考验和诱惑时精神崩溃并自杀的故事。故事中有这样一幕:一位少校在阅读年轻士兵写给心上人的绝笔信时哭得前俯后仰。故事的讲述者是一名下级士兵,也是除军官外唯一一位发现自杀现场的人。他对这位高级军官没有试图隐藏自己的情感抱以尊重:少校“只是像个妇人一样哭了起来,根本不想掩饰”。 在私密和非常情绪化的时刻,男人之间也会哭泣,即便少校也不例外。但不管怎样,哭泣就意味着“像个妇人”。事实上,吉卜林创作士兵自杀故事的全部寓意是,如果这个士兵早年就变得坚强,而不是被父母的溺爱宠坏,他就能更好地应对在印度的生活—简言之,他本可以成为一名男子汉。
“一战”以前,主流的情感风格经历了从多愁善感到自律克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有许多不同的根源。它并不是为了消除全部情感,而是为了限制情感表达的领域和方式,其中就包括公开的哭泣。1895年,也就是王尔德入狱和詹姆森突袭行动( 它为《如果—》提供了创作灵感 )的那一年,古怪的奥匈帝国医生和社会评论家马克斯·诺尔道( Max Nordau )的一本书被翻译成了英文。这本名为《堕落》的书获得了《泰晤士报》的推荐,并在报纸杂志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诺尔道认为,许多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作家都具有某种病态,他们应该像堕落的罪犯和精神错乱者一样,受到人们的怀疑。诺尔道认为,“情感主义”( emotionalism )是堕落艺术家—一个会笑到落泪或“无缘无故大哭”的人—的核心特征。平淡无奇的诗歌或绘画会让堕落者欣喜若狂,“尤其是音乐,即使最平淡乏味、不受称赞的音乐,也能唤起他最强烈的情绪”。
诺尔道的描述可以概括当时文化中的各种人物,包括理查德·瓦格纳、亨里克·易卜生和奥斯卡·王尔德。但至少有一次,他的描述似乎也适用于海报上那个紧抿上唇的家伙——基齐纳勋爵。1900年,蜚声全球的女高音歌唱家内莉·梅尔巴( Nellie Melba )和基齐纳勋爵都住在墨尔本的政府大楼里。根据梅尔巴对二人相见的描述,基齐纳自1902年起担任驻印英军总司令,直到最近才离开印度。他跪在她的面前请求道:“梅尔巴夫人,我已在外漂泊八年。您能否就为我唱一段《家,甜蜜的家》?”当她坐在钢琴前,为这位背井离乡的游子唱起这支她曾为成千上万听众吟唱的成名曲时,基齐纳一言不发,“他的脸颊上挂着两颗大泪珠”,他走上前亲吻了梅尔巴的手。 为苏格拉底之死恸哭,或为年轻战友自杀而落泪是一回事,但为《萍琪和仙女》或者《家,甜蜜的家》哭泣又意味着什么呢?诺尔道博士一定会将其诊断为堕落的情感主义。
我们相信,奥斯卡·王尔德的大儿子西里尔也是这么想的。1895年王尔德入狱时,西里尔10岁,他不久被带到国外和叔叔一起生活,他也将名字从“王尔德”改成了“霍兰德”。霍兰德后来入读拉德利学院,他在那里成了一名运动健将,是同年级最优秀的划桨手和游泳运动员,还是级长( prefect )和社团负责人。1900年的一天,他在吃早餐时从报纸上读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无意间还听到其他男孩讨论此事。这些男孩对自己的同学“霍兰德”的真实身世毫不知情。与杰弗里·戈尔在得知父亲去世后在早餐桌上抽泣不同,西里尔·霍兰德只能将悲伤藏在心里。西里尔后来在伍尔维奇的皇家军事学院受训,1905年被任命为皇家野战炮兵少尉。1914年,他在印度服役三年后擢升上尉。 同年6月,他在战争前夕写给弟弟维维安的信中,讲述了自己从小就想摆脱他们父亲名声的决心:“成为一个男人,是我的头等大事。我不应该为一个颓废的艺术家、柔弱的唯美主义者和屈辱的堕落之人哭泣。”“我不是狂放、多情和不负责任的英雄,”西里尔接着说,“我靠思想而不是情感生活。”事实上,这并不是用思想代替情感的问题,而是用另一种更爱国的情感代替一种颓废的情感的问题。他写道:“除了为国王和国家的尊严战死沙场,我别无他求。”正如他父亲笔下的一个戏剧角色所观察到的,在这个世界上,悲剧只有两种:“一种是事与愿违,另一种是得偿所愿。”1915年5月9日,西里尔·霍兰德在法国北部的纽维尔-圣瓦斯特附近被一名德军狙击手射杀。
与此同时,尽管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独生子杰克视力很弱,但得益于他大名鼎鼎的父亲的人脉,杰克被任命为爱尔兰卫队少尉。1915年8月,也就是杰克18岁生日的当月,他被派往法国执行任务。次月,他参加了洛斯战役,这场仗是对基齐纳勋爵新组建部队的第一次重大考验。两万名英军在炮弹和机枪下丧命。吉卜林少尉被报失 踪,推测已经阵亡。他的父母和他们的好友寻访了杰克的战友,试图弄清真相,但没有获得任何肯定的答复。 1 作家亨利·赖德·哈格德( Henry Rider Haggard )是寻访者之一,他的受访者中有一人确信曾看到吉卜林“试图用止血绷带缠住被炮弹弹片击碎的嘴巴”。这位士兵称自己本想去帮他,但“长官疼得直哭”,他不想因为“提供帮助而使长官蒙羞”。 十几岁的少尉打破了紧抿上唇的规则,他的眼泪使他失去了士兵的救助。你会成为一个男人,我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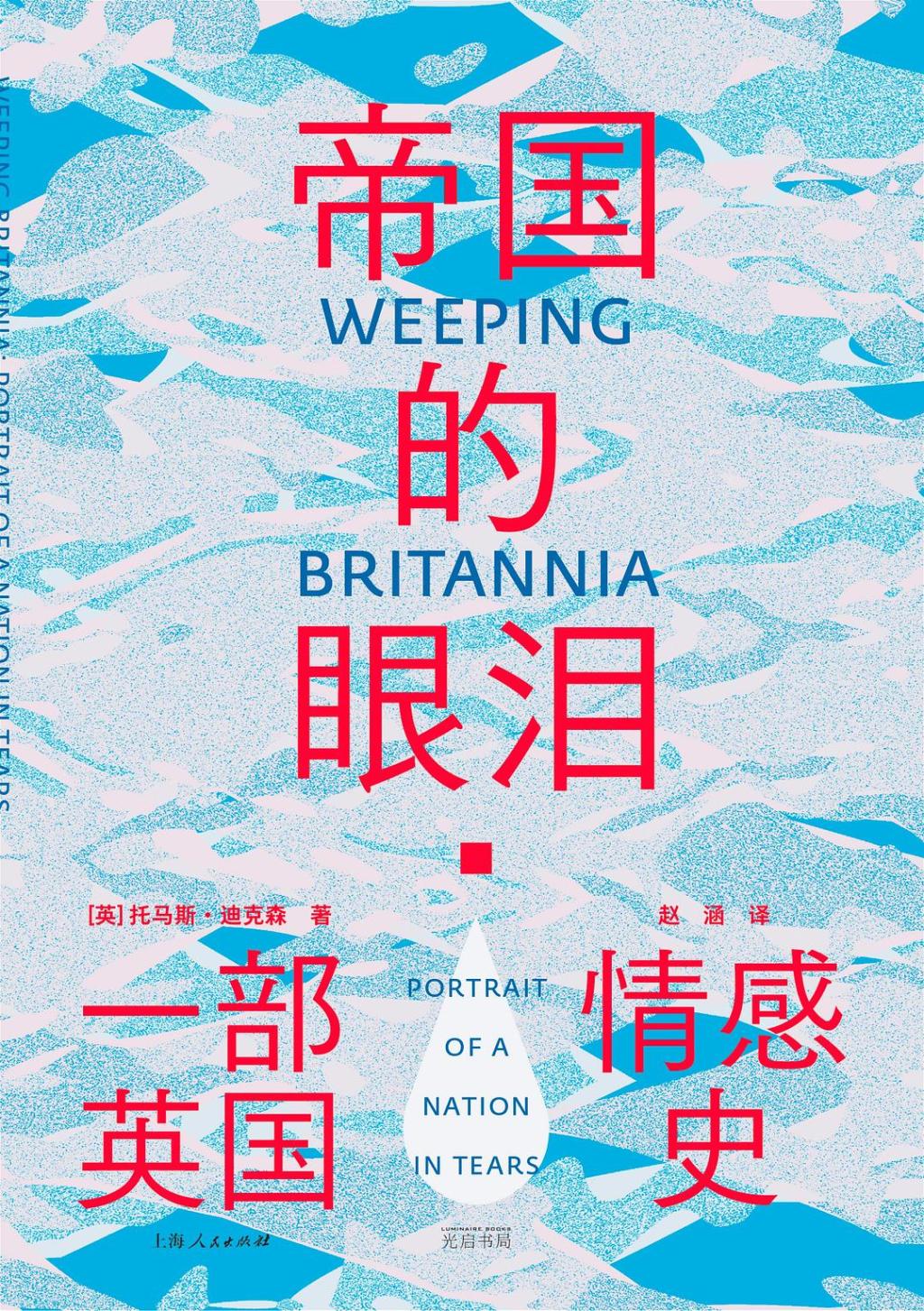
《帝国的眼泪》;作者: [英] 托马斯·迪克森;出版社: 光启书局;2025年1月版











有话要说...